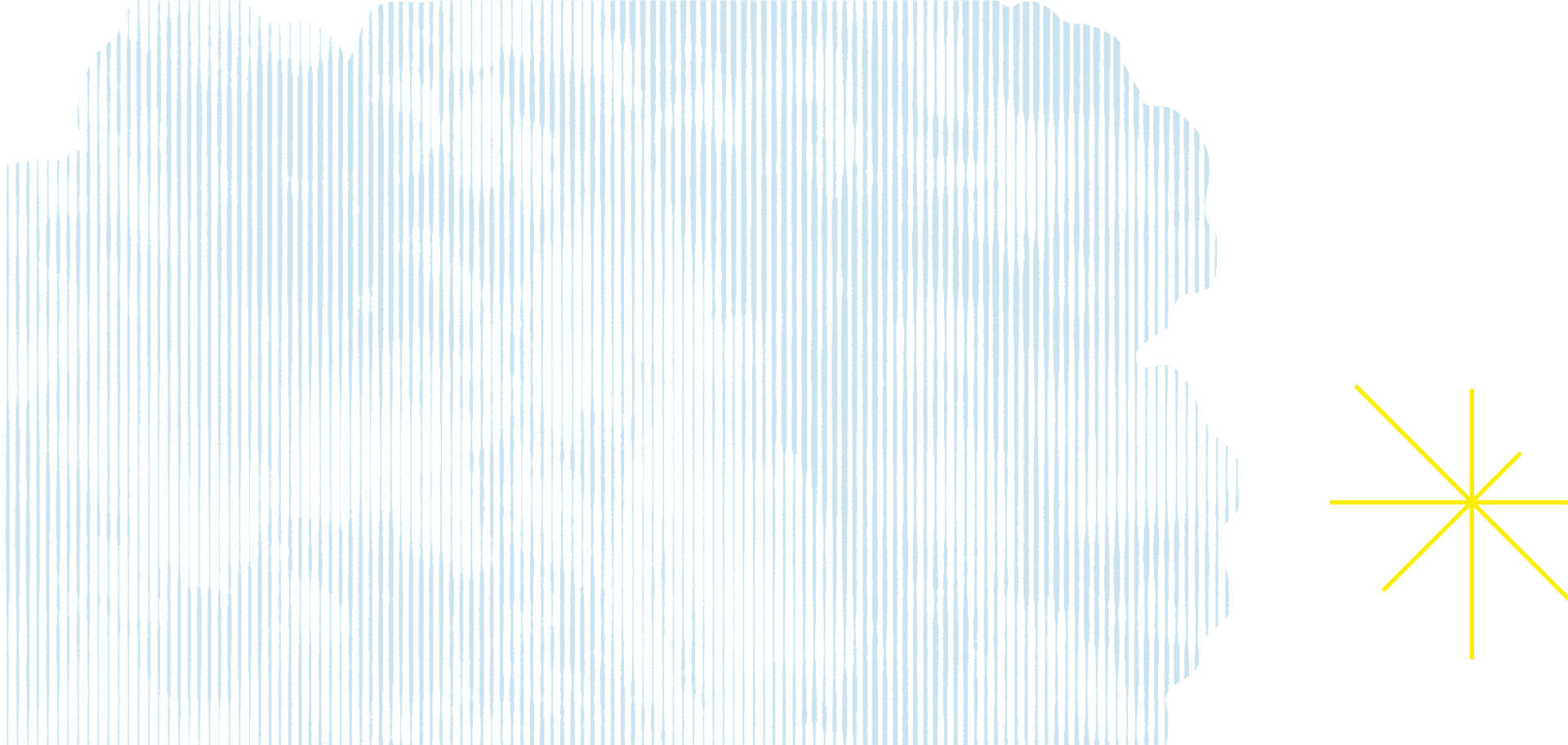部落格
2020.12.31
《搖擺.D》觀演心得:關於人的不同面向
時 間|2020年11月20日(五)19:30
編 舞|田孝慈、林祐如、楊桂娟、姚淑芬
演 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地 點|臺藝表演廳
撰 文|莊馥嘉(電影系四年級)
如《搖擺.D》的總監姚淑芬老師所說,"D" 可以被定義為 (can be defined as) 注意力分散症 (distraction disorder)、白日 (day)、黎明 (dawn) 、門與跳舞 (door and dance),而這幾個單字也緊扣著這四個舞碼——它們分別簡明扼要地闡釋每個舞碼各自傳達的意涵,《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涵蓋了日出與日落的意象,《大觀路一段59號》的隨機性帶出了潛意識中某種不斷重複再生的經驗、好似一種「症狀」,《既事、既視、既逝》以「穿」與「越」的概念進行延伸、「門」正是作為一個進出行為的形象化,《_現實之外》則以介於黑與白之間的灰色色調,呈現既貼近現實、卻也遠離現實的「真實存在」。看似隨機拼湊的四個舞作,在同樣以 "d" 開頭的單字之間,找到了彼此之間的聯集。
.png) 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
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
舞台燈暗下來,耳熟能詳的經典鬧鐘聲悠悠響起,宣告一天將正式開始。所有原先橫臥地上的、裸身的表演者們起身,穿上了衣服,可這些衣服是制式化的——大地色系的服裝款式雖有著細微的不同,但這也是唯一僅存的、可供識別每個人不同之處的微小差異——,像是某種制服或囚服,剝去每個人的個體性,要求所有人成為一個標準的人類,同樣的頭髮長度、同樣的妝容,甚至是同樣的身體與思想。
然而,人類集體中必定存在著一些「異己」——他們的行為不與集體統一,抗拒穿上放棄個體性的制服,突兀的姿態與模樣顯得怪誕而可怖:像是離開了水域,在舞台上掙扎的魚;沿著舞台邊緣奔跑,不為團體所接納的「異端份子」;又或者是嘗試加入群體、卻被無情拒斥的個體。但是,究竟是他們的本質便如此怪誕荒謬,還是這個社會的規範定義了他們的異常與偏誤,以此區分我們才是正常的一群?此兩者的對比,正是傅柯 (Michel Foucault) 於《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對於理性與瘋狂的界定:何謂理性?何謂瘋狂?當我們將行為異常的人歸納成「瘋狂」的一群,盲目服從、崇拜規範的我們,是否才是真正失去理智的一群?

就筆者的角度而言,鬧鐘聲與清晨的日光,是劃分白日與夜晚的界線,也是劃分理性與非理性的界線——在與自己獨處的夜晚,所有於白天銷聲匿跡的渴望、焦慮、不安,於夢境中席捲而來,直到陽光從窗灰濛的天空邊界傾瀉而出,我們又再度穿上制服、將自己打扮成「一般人」,彷彿那些潛意識怪物不復存在。
但是,在集體的層面上,所有表演者們面對的焦慮是共通的:如同前面無法加入群體的異己,中途突然出現在舞台上的恐龍也在舞台上瘋狂地奔跑,搭配著預錄好的聲音,喃喃低語著白堊紀的歷史:「6,500萬年前,小行星撞擊地球,恐龍毀滅。200萬年前,第一個人類出現了。」緊接著,表演者聚集在一塊,堆砌起一道逐步攀升的人牆,好似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演化論的再現,狀態混沌不明的人猿,演變成帶有強烈自我意識的現代人——我們由哺乳類演化而來,哺乳類是爬蟲類的前身......兩棲類是水生動物上岸前的過渡型態,水生動物更早以前是單細胞生物......而單細胞生物以前,世界是一片無盡黑暗的大陸。在演化過程中,表演者繼承了前一代生物與祖先的遺跡,延續至今,向觀眾展現所有人類共有的焦慮與恐懼。
「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或許我們是人,是爬蟲類,也或許是整個世界。
.png) 大觀路一段59號
大觀路一段59號
表演者在灰暗、冷峻、工整的舞蹈教室內,開始了一天忙碌的練習。接著四周的燈光於轉瞬間一改先前抑鬱灰冷的色調,溫暖如午後的陽光充斥舞台上的所有角落,邀請觀眾進入屬於舞蹈學系學子們的想像空間裡。
舞蹈學系的片刻與生活日常,零零總總組成了《大觀路一段59號》——各式各樣在劇場中的發聲練習,來回走動,低吼,忙碌於此端,忙碌於彼端。在《大觀路一段59號》的舞台上,跳舞是表演者們唯一企求的事情:舞蹈在長久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地練習與實踐後,不再是一種出於編舞者的意志而引發的動作指令,也不再是一種無意識而盲目的服從行為,而是一種本能的、與生俱來的經驗。
心理分析學家拉岡 (Jacques Lacan) 曾經提出這樣的疑問:「你的行動一致於你的欲望嗎?」 (Have you acted in conformity with your desire?)。當拉岡如是問道時,他主張人們應回歸最原初的死亡驅力 (death drive),也就是當一個人意欲死亡時,他並不思考死亡將帶予他什麼樣的痛苦,或是將他的死亡提升到神聖的犧牲,而是張開雙臂、迎接那不可逃離的死亡,讓死亡完全地貫穿自己、進入自己的體內。

筆者認為,《大觀路一段59號》同樣展現了一種純粹的欲望當表演者一一地來到舞台上——身著綠色衣服的女孩不斷地左右來回踱步、雙臂如鐘擺般擺動,身著白衣的女孩仰躺在地上扭動、好似被一條隱形的魚線操縱著——,不斷重複著相同的動作、重複相同的話語,彷彿暗示著這一切都是毫無理由的、非理性的,動作背後本身並不存在著任何意義、也不存在任何動機。表演者們遵從他們的意欲跳舞、意欲行動的本能,不逃避亦不抗拒,而是接受它們的引領。這一刻,表演者們的動作與背後的運作機制完全重疊:他們行動,出自於最純粹的想要行動的欲望,同樣地,他們跳舞,也出自於純粹想要跳舞的欲望。此刻,他們實踐了拉岡的呼籲。
最後,舞台上的一切逐漸復歸平靜,表演者們回到了最初的舞蹈教室裡——日常而瑣碎的排舞片刻持續地進行著,以期來日與舞蹈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體。
.png) 既事、既視、既逝
既事、既視、既逝
每個人在與許多人的關係之中,總是能不斷地看到來自過往的似曾相識的陰影。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曾經提出「強迫性重複」(Repetitive Compulsion) 的概念——佛洛伊德認為,人們在經歷過某種創傷性事件後,會不斷地在往後其他的生命事件中強迫性地回歸當年的創傷情景。強迫性重複或許聽來像是某種難以理解的被虐傾向,然這種傾向卻意外地能給予創傷的主體莫大的安全感。
《既事、既視、既逝》以一位紅衣女舞者貫穿三個舞作核心——親情、友情與愛情——,不同的生命事件與生命主體,卻由同一位舞者展現所有發酵於其中的感受。「你最近在忙什麼?」「最近還好嗎?」——這些由字面判斷,應是溫暖而讓人感到放心的問句,卻與《既事、既視、既逝》中與不斷出現的傘共同指向了同一件事情。親情、友情與愛情,或許只是千萬種生命面貌的簡化與歸納,但是若仔細探究下去,我們發現自己始終都困在這三個抽象卻也再明確不過的情感裡。

我們不能否認,在各自的生命歷程裡、我們始終無以逃離這三個議題。三者的出發點雖然都是愛,但是愛可能是窒息的、控制的、難以忍受的、瘋狂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如同那把不斷出現的傘,撐著傘的人、拋接傘的人各有所不同,但是他們籠罩在紅衣舞者頭頂上的陰影卻不曾缺席。在《既事、既視、既逝》中,我們發現生命中並非存在著千萬種面向,而是所有樣貌皆由同一種情感——也就是「愛」——所衍生出來。「愛」僅是以變形的樣貌出現,而所有情感的本質皆是愛。
於是,筆者終於能夠明白,為什麼《既事、既視、既逝》選擇以同一位紅衣舞者展現三種情感,即便她並非這些生命經驗的當事人:也許正如佛洛伊德所述,由於情感的本質相同,而使得我們在友情中、亦可以看見愛情或是親情的元素,而愛情之中亦能發現其他兩者的痕跡。我們終其一生不斷地重複最原初的創傷情境,以滿足埋藏在靈魂深處的對於愛與痛的渴求。
.png) _現實之外
_現實之外
若說《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透過展示個人及集體的身體,反覆審視作為集體生物的「人」的模樣,作為繼承遠古及過去記憶的「人」又是什麼模樣,那麼《_現實之外》同樣透過人的身體,審視及實驗人的某種特質。
《_現實之外》的開頭,畫著灰白色的妝容、掛著毫無血色的雙唇、被剝奪靈魂的空洞雙眼的表演者聚集在一起,仿佛一群未知的群聚生物——我們無法否認,表演者的狀態及模樣,無從與我們想像中的「人類」產生連結。他們透過肢體的交纏、軀體的重合建立物理性的、可見的連結,而非以我們日常習慣的言語進行「交談」。
表演者陌生、與人類相去甚遠的模樣,讓筆者想起韓國雕塑家崔秀仰 (Choi Xooang) 的作品:崔秀仰將人的面孔及胴體進行超寫實主義式 (Hyperrealism) 的描繪,同時將木棍、根莖等(非)有機體與人體融合。於是,在崔秀仰多數的作品中,人與物之間的界線消弭於無形——我們無法在其作品中確切判斷這些存在究竟是人、動物,是非人、或是其他未知的生物。
姚淑芬在《_現實之外》中讓表演者的身體相互交疊,攀爬到對方的身上,以極度耗費力量的方式跳躍,剝除他們身上所有可供判斷為「人」的人性及特質,迫使觀者在整場表演的進行過程中不斷地回歸之所以使我們存在的問題:「我是誰?從哪裡來?將往何處去?」(Wer bin ich? Woher komme ich? Wohin gehe ich?) 我們的存在,究竟是在提問自身的存在時產生——意味著若我們不曾提問,我們便從來不存在——,亦或是我們的存在自始至終都不曾是需要被驗證的事實?但是,當我們看見《_現實之外》中似人非人的存在,我們是否還能對自身的本質感到如此自信?
舞作的結尾,天上緩緩罩下一塊白紗,將所有的表演者包裹其中:或許如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當初創造了人類,如今他也創造了舞台上這一群難解的存在。現在,普羅米修斯將要在一切來到終點之際「收回」他們。 【搖擺.D】作品之一《_現實之外》片段 攝影 游翔皓
【搖擺.D】作品之一《_現實之外》片段 攝影 游翔皓
隨著《_現實之外》的結束,舞台上始於 "d" 的一切——從直觀意義上的 "dance",乃至於與舞作有所關聯的各個單字——,也於 "d" 結束。如 "degeneration" 一詞意味著「蛻變」,同時意味著「退變」、「衰退」:不論對表演者或觀者而言,《搖擺.D》的共同經驗皆是一場「蛻變」的過程。表演者們在舞台上以具象化的方式演繹現實生活裡難以言說、難以名狀的事物,為觀者開啟了對於人的根源、存在的意義、渴望以及本質的視野與洞察。然而,表演的結束也是一場「退變」。生命/開始的存在,同時暗示了死亡/結束的不可避免。不過,"degeneration" 的二元性讓開始與結束於這個場域裡相遇,與 "dance" 一同串接了其中所有的事件與主體,讓生命與死亡週而復始地發生,一切並不真正開始、也非真正結束。
表演者們在當下的即時性裡對我們所展示出的、對於何謂「人」的提問,同樣不會隨著他們回歸普羅米修斯的懷抱或回到日常而消逝。一旦開啟了對於自身的提問,我們便將帶著這份疑問生活下去,成為縈繞我們心頭而揮之不去的永恆刺點(Punctum)。
編 舞|田孝慈、林祐如、楊桂娟、姚淑芬
演 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地 點|臺藝表演廳
撰 文|莊馥嘉(電影系四年級)
如《搖擺.D》的總監姚淑芬老師所說,"D" 可以被定義為 (can be defined as) 注意力分散症 (distraction disorder)、白日 (day)、黎明 (dawn) 、門與跳舞 (door and dance),而這幾個單字也緊扣著這四個舞碼——它們分別簡明扼要地闡釋每個舞碼各自傳達的意涵,《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涵蓋了日出與日落的意象,《大觀路一段59號》的隨機性帶出了潛意識中某種不斷重複再生的經驗、好似一種「症狀」,《既事、既視、既逝》以「穿」與「越」的概念進行延伸、「門」正是作為一個進出行為的形象化,《_現實之外》則以介於黑與白之間的灰色色調,呈現既貼近現實、卻也遠離現實的「真實存在」。看似隨機拼湊的四個舞作,在同樣以 "d" 開頭的單字之間,找到了彼此之間的聯集。
.png) 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
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舞台燈暗下來,耳熟能詳的經典鬧鐘聲悠悠響起,宣告一天將正式開始。所有原先橫臥地上的、裸身的表演者們起身,穿上了衣服,可這些衣服是制式化的——大地色系的服裝款式雖有著細微的不同,但這也是唯一僅存的、可供識別每個人不同之處的微小差異——,像是某種制服或囚服,剝去每個人的個體性,要求所有人成為一個標準的人類,同樣的頭髮長度、同樣的妝容,甚至是同樣的身體與思想。
然而,人類集體中必定存在著一些「異己」——他們的行為不與集體統一,抗拒穿上放棄個體性的制服,突兀的姿態與模樣顯得怪誕而可怖:像是離開了水域,在舞台上掙扎的魚;沿著舞台邊緣奔跑,不為團體所接納的「異端份子」;又或者是嘗試加入群體、卻被無情拒斥的個體。但是,究竟是他們的本質便如此怪誕荒謬,還是這個社會的規範定義了他們的異常與偏誤,以此區分我們才是正常的一群?此兩者的對比,正是傅柯 (Michel Foucault) 於《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對於理性與瘋狂的界定:何謂理性?何謂瘋狂?當我們將行為異常的人歸納成「瘋狂」的一群,盲目服從、崇拜規範的我們,是否才是真正失去理智的一群?

【搖擺.D】作品之一《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片段 攝影 游翔皓
就筆者的角度而言,鬧鐘聲與清晨的日光,是劃分白日與夜晚的界線,也是劃分理性與非理性的界線——在與自己獨處的夜晚,所有於白天銷聲匿跡的渴望、焦慮、不安,於夢境中席捲而來,直到陽光從窗灰濛的天空邊界傾瀉而出,我們又再度穿上制服、將自己打扮成「一般人」,彷彿那些潛意識怪物不復存在。
但是,在集體的層面上,所有表演者們面對的焦慮是共通的:如同前面無法加入群體的異己,中途突然出現在舞台上的恐龍也在舞台上瘋狂地奔跑,搭配著預錄好的聲音,喃喃低語著白堊紀的歷史:「6,500萬年前,小行星撞擊地球,恐龍毀滅。200萬年前,第一個人類出現了。」緊接著,表演者聚集在一塊,堆砌起一道逐步攀升的人牆,好似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演化論的再現,狀態混沌不明的人猿,演變成帶有強烈自我意識的現代人——我們由哺乳類演化而來,哺乳類是爬蟲類的前身......兩棲類是水生動物上岸前的過渡型態,水生動物更早以前是單細胞生物......而單細胞生物以前,世界是一片無盡黑暗的大陸。在演化過程中,表演者繼承了前一代生物與祖先的遺跡,延續至今,向觀眾展現所有人類共有的焦慮與恐懼。
「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或許我們是人,是爬蟲類,也或許是整個世界。
.png) 大觀路一段59號
大觀路一段59號表演者在灰暗、冷峻、工整的舞蹈教室內,開始了一天忙碌的練習。接著四周的燈光於轉瞬間一改先前抑鬱灰冷的色調,溫暖如午後的陽光充斥舞台上的所有角落,邀請觀眾進入屬於舞蹈學系學子們的想像空間裡。
舞蹈學系的片刻與生活日常,零零總總組成了《大觀路一段59號》——各式各樣在劇場中的發聲練習,來回走動,低吼,忙碌於此端,忙碌於彼端。在《大觀路一段59號》的舞台上,跳舞是表演者們唯一企求的事情:舞蹈在長久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地練習與實踐後,不再是一種出於編舞者的意志而引發的動作指令,也不再是一種無意識而盲目的服從行為,而是一種本能的、與生俱來的經驗。
心理分析學家拉岡 (Jacques Lacan) 曾經提出這樣的疑問:「你的行動一致於你的欲望嗎?」 (Have you acted in conformity with your desire?)。當拉岡如是問道時,他主張人們應回歸最原初的死亡驅力 (death drive),也就是當一個人意欲死亡時,他並不思考死亡將帶予他什麼樣的痛苦,或是將他的死亡提升到神聖的犧牲,而是張開雙臂、迎接那不可逃離的死亡,讓死亡完全地貫穿自己、進入自己的體內。

【搖擺.D】作品之一《大觀路一段59號》片段 攝影 游翔皓
筆者認為,《大觀路一段59號》同樣展現了一種純粹的欲望當表演者一一地來到舞台上——身著綠色衣服的女孩不斷地左右來回踱步、雙臂如鐘擺般擺動,身著白衣的女孩仰躺在地上扭動、好似被一條隱形的魚線操縱著——,不斷重複著相同的動作、重複相同的話語,彷彿暗示著這一切都是毫無理由的、非理性的,動作背後本身並不存在著任何意義、也不存在任何動機。表演者們遵從他們的意欲跳舞、意欲行動的本能,不逃避亦不抗拒,而是接受它們的引領。這一刻,表演者們的動作與背後的運作機制完全重疊:他們行動,出自於最純粹的想要行動的欲望,同樣地,他們跳舞,也出自於純粹想要跳舞的欲望。此刻,他們實踐了拉岡的呼籲。
最後,舞台上的一切逐漸復歸平靜,表演者們回到了最初的舞蹈教室裡——日常而瑣碎的排舞片刻持續地進行著,以期來日與舞蹈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體。
.png) 既事、既視、既逝
既事、既視、既逝每個人在與許多人的關係之中,總是能不斷地看到來自過往的似曾相識的陰影。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曾經提出「強迫性重複」(Repetitive Compulsion) 的概念——佛洛伊德認為,人們在經歷過某種創傷性事件後,會不斷地在往後其他的生命事件中強迫性地回歸當年的創傷情景。強迫性重複或許聽來像是某種難以理解的被虐傾向,然這種傾向卻意外地能給予創傷的主體莫大的安全感。
《既事、既視、既逝》以一位紅衣女舞者貫穿三個舞作核心——親情、友情與愛情——,不同的生命事件與生命主體,卻由同一位舞者展現所有發酵於其中的感受。「你最近在忙什麼?」「最近還好嗎?」——這些由字面判斷,應是溫暖而讓人感到放心的問句,卻與《既事、既視、既逝》中與不斷出現的傘共同指向了同一件事情。親情、友情與愛情,或許只是千萬種生命面貌的簡化與歸納,但是若仔細探究下去,我們發現自己始終都困在這三個抽象卻也再明確不過的情感裡。

【搖擺.D】作品之一《既事、既視、既逝》片段 攝影 游翔皓
我們不能否認,在各自的生命歷程裡、我們始終無以逃離這三個議題。三者的出發點雖然都是愛,但是愛可能是窒息的、控制的、難以忍受的、瘋狂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如同那把不斷出現的傘,撐著傘的人、拋接傘的人各有所不同,但是他們籠罩在紅衣舞者頭頂上的陰影卻不曾缺席。在《既事、既視、既逝》中,我們發現生命中並非存在著千萬種面向,而是所有樣貌皆由同一種情感——也就是「愛」——所衍生出來。「愛」僅是以變形的樣貌出現,而所有情感的本質皆是愛。
於是,筆者終於能夠明白,為什麼《既事、既視、既逝》選擇以同一位紅衣舞者展現三種情感,即便她並非這些生命經驗的當事人:也許正如佛洛伊德所述,由於情感的本質相同,而使得我們在友情中、亦可以看見愛情或是親情的元素,而愛情之中亦能發現其他兩者的痕跡。我們終其一生不斷地重複最原初的創傷情境,以滿足埋藏在靈魂深處的對於愛與痛的渴求。
.png) _現實之外
_現實之外若說《一些事情的切片,與人相關》透過展示個人及集體的身體,反覆審視作為集體生物的「人」的模樣,作為繼承遠古及過去記憶的「人」又是什麼模樣,那麼《_現實之外》同樣透過人的身體,審視及實驗人的某種特質。
《_現實之外》的開頭,畫著灰白色的妝容、掛著毫無血色的雙唇、被剝奪靈魂的空洞雙眼的表演者聚集在一起,仿佛一群未知的群聚生物——我們無法否認,表演者的狀態及模樣,無從與我們想像中的「人類」產生連結。他們透過肢體的交纏、軀體的重合建立物理性的、可見的連結,而非以我們日常習慣的言語進行「交談」。
表演者陌生、與人類相去甚遠的模樣,讓筆者想起韓國雕塑家崔秀仰 (Choi Xooang) 的作品:崔秀仰將人的面孔及胴體進行超寫實主義式 (Hyperrealism) 的描繪,同時將木棍、根莖等(非)有機體與人體融合。於是,在崔秀仰多數的作品中,人與物之間的界線消弭於無形——我們無法在其作品中確切判斷這些存在究竟是人、動物,是非人、或是其他未知的生物。
姚淑芬在《_現實之外》中讓表演者的身體相互交疊,攀爬到對方的身上,以極度耗費力量的方式跳躍,剝除他們身上所有可供判斷為「人」的人性及特質,迫使觀者在整場表演的進行過程中不斷地回歸之所以使我們存在的問題:「我是誰?從哪裡來?將往何處去?」(Wer bin ich? Woher komme ich? Wohin gehe ich?) 我們的存在,究竟是在提問自身的存在時產生——意味著若我們不曾提問,我們便從來不存在——,亦或是我們的存在自始至終都不曾是需要被驗證的事實?但是,當我們看見《_現實之外》中似人非人的存在,我們是否還能對自身的本質感到如此自信?
舞作的結尾,天上緩緩罩下一塊白紗,將所有的表演者包裹其中:或許如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當初創造了人類,如今他也創造了舞台上這一群難解的存在。現在,普羅米修斯將要在一切來到終點之際「收回」他們。
 【搖擺.D】作品之一《_現實之外》片段 攝影 游翔皓
【搖擺.D】作品之一《_現實之外》片段 攝影 游翔皓隨著《_現實之外》的結束,舞台上始於 "d" 的一切——從直觀意義上的 "dance",乃至於與舞作有所關聯的各個單字——,也於 "d" 結束。如 "degeneration" 一詞意味著「蛻變」,同時意味著「退變」、「衰退」:不論對表演者或觀者而言,《搖擺.D》的共同經驗皆是一場「蛻變」的過程。表演者們在舞台上以具象化的方式演繹現實生活裡難以言說、難以名狀的事物,為觀者開啟了對於人的根源、存在的意義、渴望以及本質的視野與洞察。然而,表演的結束也是一場「退變」。生命/開始的存在,同時暗示了死亡/結束的不可避免。不過,"degeneration" 的二元性讓開始與結束於這個場域裡相遇,與 "dance" 一同串接了其中所有的事件與主體,讓生命與死亡週而復始地發生,一切並不真正開始、也非真正結束。
表演者們在當下的即時性裡對我們所展示出的、對於何謂「人」的提問,同樣不會隨著他們回歸普羅米修斯的懷抱或回到日常而消逝。一旦開啟了對於自身的提問,我們便將帶著這份疑問生活下去,成為縈繞我們心頭而揮之不去的永恆刺點(Punctum)。